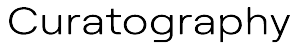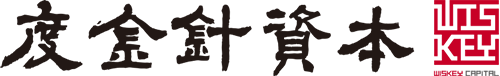策展一向咸信為特定的專業實踐,需具備理性、直覺和情感的特殊能力,而不是簡單地被歸類為單一學門。雖然策展涉及藝術、藝術史、人類學、社會學、媒體與文化研究等領域知識,但「策展」的發展其實早已超越了傳統學科框架。近年來,隨著各種不同「策展內容」(content curating)的出現,策展課題不再侷限於藝術,而是延伸到流行文化、香水、檔案、音樂、食物、廣告、商品、形象,甚至還包含各樣的社會現象。策展早已經是跨領域的文化實踐,而非原本的學術分類。整體來說,策展的功能就是把「過剩象徵文化」(symbolic cultural excesses)進行排置與次序化。1 正如邁克・巴斯卡(Michael Bhaskar)所說:「策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種『過剩』需要被言說、被接受。」2 舉例而言,傳統美術館的展示方式體現了這種秩序配置:重要的作品通常擺在觀眾平視的位置,次要的則放在上方或下方。而到了今日的盛行「線上策展」,展示邏輯也從「水平」轉為「垂直」:重要作品配置在網頁上方,不重要的內容在下方, 須滑動才能被看見。
不管是水平或垂直(或任何非視覺的次序),「啟蒙時期」是第一個顯現大規模文化過度的歷史時期,策展是將這個世界次序化的規訓之一:在工業革命、殖民主義發展中,顯示過剩以及異國情調的物件,並將商品在金錢價值之外所需要的脈絡敘事,以誇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方式,進行劣化。人類對於「次序化」所產生的執念之最好證據, 正是在270年前開始許多的個人、機構、及商業的線上/實體策展;但此「次序化」不僅是策展人將過剩物件價值化的過程, 例如在金錢、美學、社會、文化或歷史等等各個層面,更是遠遠超過地,言說了生命的任意性,編織成表面爲自明的故事。然而,實際上卻強制在連貫的標題與次標題之下的不連續情節;創造了斷裂、不連續的文化實踐之傳奇與敘事;而那些如謎、看似哲理的名家話語引言更強化了這種敘事性的操作。
在全球當代策展文化中,「次序/戒令」3(order)正蓬勃多樣的發生中,經由特定的文化觸媒,如策展人或策展團隊以「次序/戒令」(order)的姿態, 指派那些需要被研究、發現、說明、言談、展演、意識形態化、評價、消費、導覽、儲藏或遺忘等等的項目。如此的文化觸媒逐漸形成一種成長中的威權權力,化身為展覽組織者與藝術總監的角色,透過資金贊助、藏家與捐助者,以統治者角色以特定權力次序維繫特定時間的支配(如某特定典藏或展覽)。在這種情境下,策展的權力將持續成長——只要全球性經濟不陷入蕭條,這個無止境的生產/消費迴圈會繼續依循特定次序轉動,例如「沒有新的展覽」的斷裂就是異常。隨著「AI人工智慧」進化,策展作為專業技術, 會成為一連串搜尋指令的集合,屆時也許不再存在以「次序化」為核心的「過剩象徵文化」,相關的策展權力也可能不再擴大。
那麼,策展能否採用差異次序,並成為「差異實踐」?
回應楊硯奇的問題:「還能做什麼?」4, 第一部分的回應:策展還有另一種次序的可能,那是一種更自然的次序。這裡所說的自然,並非指物質世界或環境,而是指一種已被結構化的無政府之自然次序。如同對無政府主義與「類」無政府主義的理解,「無政府」或「安那其」理應視為一種次序(就像倫敦街頭的塗鴉,A 被畫在 O 裡面)。策展的方向應是:無政府就是自然的次序。回應楊問題的第二部分,則是應當削減策展的階層制,讓所有人都能貢獻,一起生成展覽,不論是憑藉個人的知識或品質。根據策展人的意願,策展的權力理應是平面的結構。 從這兩個概念發展「策展無政府」的想法,並非意指我們不需要策展人,或不需要自然次序,也不是要否定他們在平面結構中的角色,而是指出策展可以由此發展出差異性實踐的可能, 一種依循自然與水平邏輯的方式。
我將從簡要地定義關鍵詞彙開始,藉此回應這個問題。請注意:(a)本文僅是邁向更擴延分析的基礎扎記,因此接下來所提的概念仍在成形之中;(b)文章的標題是無政府的「初探」(towards),而非「無政府主義」,後者是一套政治理念體系,內部有著眾多分歧與路徑(例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非裔族群實踐等),以及具體實踐形式(如聯邦制、互助勞動等),接下來必須釐清「無政府」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區別;(c)我也將引用無政府主義中的若干重要人物,但這並不代表我接下來的分析將對「無政府」或「象徵文化過度」作出全面總結,5 更不用說策展及其次序化任務,本來就符合市場機制中多樣的流行趨勢與品味的生產消費邏輯。
I. 詞彙
自然次序:跟隨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詮釋,「自然次序」沒有對錯之分,也無特定規範條件。6 這是相當弔詭的,因為「自然次序」本身包含了誤導的因果關係、模式錯誤與混亂。因此,秩序不可能在清晰的架構中發生,自然秩序必須發生於混沌之中。它不是一個系統,也不是一個網絡,因為這兩者都預設了特定的線性結構、管理指令,或是自我學習的次序工作。自然次序必須面對所有的「此有」(ontic,包含生物、宇宙觀、歷史等)、「存有」(ontological)以及終極的進化, 涵蓋著各樣的應變擴張與緊縮、單一與多元的宇宙,以及相關規模、起源與目的。這並非一種系統或演化邏輯,自然次序是一種渾然天成的動能;也就是說,自然擴展之必要,並非源自於既定形式的衍生。7 因此,自然次序沒有任何外部,一如風景與環境;自然次序是一種能量的釋出,而非宿命的邏輯,這正是自然的運作方式。
無政府:學者一致認為,無政府並非如一般所理解的混亂狀態,也不是缺乏秩序的表徵。無政府並非是藉由強制力維持的人為秩序,而是自然且必要的生成秩序。正因如此,無政府指涉的是自然與內在必然的次序性,它代表大自然在能量持續介入下對自身的再創造。「混亂」與「違法」等詞彙常被誤認為是無政府的同義詞;然而事實上,我們必須認識:無政府本身就是秩序。無政府是自然次序的必要過程,不受任何超越其自身的外在權力所干預。對社會層面而言,「無政府」意味著沒有統治者與強制力的介入。一些具體例子或可幫助理解這個觀點:雨林生態、朋友圈、自身的身體、冠狀病毒期間的互助團體、共享育幼服務、無政府社群,乃至非階層權力、自然生成的「組織」。「無政府」建立於自然主義與應變唯物主義之上,這正是得自於史賓・諾莎的靈感。
II. 無政府不是炸彈客、反社會、理想主義
先從否定開始,以「炸彈客」為例,「政府」其實才是唯一的暴力組織:他們擁有最大規模的軍火庫,也能以無責無罪的方式進行暗殺。俄國與以色列都是近的案例, 可以清楚地說明了政府的「集體暴力」。正如人類學家布萊恩・莫里斯(Brian Morris)所言:「這一世紀以來,自由主義政客與媒體,不是出於惡意的無知,就是基於政治口號,總把無政府描繪成一種暴力的炸彈客行動,好像一般政府本身從未如此。」8「無政府策展」的意義, 不是觀眾向展覽擲炸彈,也不是策展人應該手持手榴彈,更不是展覽須呈現破壞性質的作品。事實上,真正持續壟斷與行使暴力的,一直都是政府與其同步的權力結構——他們透過政治與宗教的名義,實現暴力的合法化。
「無政府」與「無政府策展」並不是對社會性或社會互動的否定,更不是戲謔或諷刺地破壞社會道德,也絕非社會層面的恐怖攻擊。相反地,「無政府」本身是一種特定「社會性」(sociality)的顯現;但這種社會性須與「自然」緊密配對,且不容有階級化的權力介入。只要存在階級制度,人與人之間便無法建立真正的合作關係,僅剩下服從於如教宗、國王、總統、首相等上位者的。因此,「無政府」是一種去除契約的壓迫結構之社會性。9 而「無政府策展」則是非階層、非威權的社會實踐,進而重新界定當代世界與文化過剩中的次序, 例如對美術館委員會、館長、財政委員、藝術總監、策展人等結構性權力的重新認識與重組。
相同地,無政府是一種非階層制度的社會性,也是一種與他人之間互相影響的狀態;它所瓦解的,僅是那些掌握過多權力的「他人」所建立的權力結構。憲章與法律,往往正是為這些人而設計的,是透過決斷力所建立的階層制度。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恩瑞哥・馬拉特斯塔(Enrico Malatesta)曾說:「我們不假裝要瓦解自然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影響,我們要瓦解的,是不自然的人為影響,那些包含特權、司法與官僚的制度。」10 在無政府狀態中,雖無自然的權力架構,然而「力與力」之間的拉鋸依然存在。將策展視為一種政府形式,並非要消除專家與專業,而是要瓦解特權對無權之他者的壟斷,解除文化過程與次序建構中被特定群體壟斷的權力, 這可以從動物主義及陽具中心主義的運作觀察得知。
「無政府」常被視為一種過度理想的產物,永遠無法實現,其原因在於人性總被認為傾向於特定形式的主宰與統治。然而,無政府並非發生於某個遙遠且未知的未來;若如此,我們便是將無政府主義當成如同共產主義一般的, 具有某種終極目標,反而違背其當下生成、即時實踐之潛能。對無政府而言,並不存在一個遙遠的未來,因為它就在此時此刻。對我們而言,無政府是逃離威權與特權,自我組織的社會實踐方式。也因此,無政府至今尚未真正進入人類意識的核心,但一旦進入,便等同於進入了「一種自然次序。」11 同樣地,「無政府策展」並非一種寄託於未來的烏托邦想像,而是在我們已經意識到當某些藝術家被高高舉起、而另一些則被拋入歷史的晦暗鏡子時,我們必須開始拒絕、抵抗,甚至鄙視那些將策展簡化為雙年展、三年展、藝術博覽會等標準化展覽操作模式。我們必須在當下時刻中生成「無政府策展」的行動姿態,不斷提醒我們:遙遠的「理想」並不存在,正在發生中「無政府」反倒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對象。
III. 無政府即次序
提出一個正面的宣告:什麼是無政府?為什麼「無政府」就是次序?探求其字源學意義: an- 意為「無」,arkhos 則是「領導者」,源自 arkhein 的現在分詞,意指「開始於…」。因此,無政府的核心概念在於「無引領的開端」,拒絕威權。12「無政府」主張互質性、變異性以及去除既定法則等等能力來確立自身,而非仰賴任何的人設的虛假威權系統。這也正是無政府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它試圖回應這個關鍵問題: 如何讓多元而變動的社會自然地生成秩序,而不是依賴某個統治者及其特權所主導的架構?而我們所關注的,正是「無政府」如何提出對世界次序化的全新理解,而非某些特權化個人的威權位置所界定的秩序。
自成一格、原創性學者安森・貝勒加里格(Anselme Bellegarrigue)是第一位提出「無政府就是次序,而政府就是內戰」的無政府主義者。13 我們必須強調,正是貝勒加里格這句著名的話語首次挑戰了「政府作為機構化秩序」這樣根深蒂固的常識性觀念。14 往往,「常識」才是最危險的,「常識」必須被持續質疑與鬆動其基礎。這種挑戰不只是語言上的修辭操作,而是對我們深信「沒有政府主體,生活便無法運作」的集體預設之顛覆。因此,我們不僅該詢問:變異性與互質性是否能在無階層的條件下自行組織?我們更應該警覺依附於「掌權者」的次序之錯誤信念。無政府並非混亂,而是一種由多元、非階層、非命令邏輯所構成的次序實踐。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謬誤:「政府是為了避免混亂而產生」。 這個陳腔濫調不過是建立在一種對「外部力量」的想像之上:即只有某種在體制之外的力量,才能維持秩序。更精確地說,人們之所以將無政府視為混亂,是因為相信世界的秩序來自某種「開端」(archē), 一種抑制性的、原則性的、或物質性的起源力量。這種「開端」觀念明顯來自宗教,它代表一種非混亂的神性或超驗主體,是秩序的化身。而在這種觀點中,「無政府」則被視為與神性秩序相對立的混亂狀態,是必須被驅逐的敵對力量。這個外在的幽靈正是所謂的「開端」, 必須將一切現實中內在的行動力視為無序與危險的來源。這種思維最終導向的結論是:必須有一位統治者來修正、改善這種混亂。而統治者之所以擁有這種能力,是因為他被想像來自神或王國的威權,作為「天選之人」,並透過那個虛構的「開端」 與承襲威權,統治者成為人民秩序的建立者與保證者, 並擁有「合理」的正當性。
治理權自動伴隨著「天選」過程; 例如, 教宗、皇帝、國王一般,成為一位被指派(而非天選)的統治者——是階層體系中的一環,承襲某種來自太古的權力「開端」。15 正如無政府主義哲學家皮耶-約瑟夫・普宏(Pierre-Joseph Proudhon)所言:「政府與秩序之間如同因與果的關係;政府是因,秩序為『果』。」16 因此,統治者的權力乃是透過一種看似無可置疑的因果邏輯,將人民的意志扭曲為「神聖秩序」或戒律的象徵。儘管在美術館與畫廊中未必存在「天選」的場景,這種階層性的邏輯卻不斷在各種藝文機構中複製與重演:某些人被視為秩序維護者,其角色不僅針對展覽本身,也針對穩定與運作順暢的藝術機制。17
IV. 序列與配置
當「無政府次序」已如藍圖般是細緻的部署,我們有必要突顯它與今日主流所詮釋的「次序」之間的根本差異。正如普宏(Proudhon)所指出,當代我們所見的次序,往往是透過系列與對稱排列所設計構成,看似合理,其實只是為了製造出一致性的幻象。18 其實, 「序列」的建立是「非」邏輯性,而是透過比重、測量來構成其自身一致性的屬性。對稱、安排、序列等實際上是物件之間關係。因而,展覽中作品的對稱編排,會帶給部分作品一種愉悅感,讓整體展覽適合觀賞。但這正是統治者的次序,將多樣多元的社會壓抑為整齊的一致性,而非召喚自然的「開端」。在策展中,這種傾向更為明顯:展覽常以一連串視覺序列構成表面的條理性,使人誤以為所見即為秩序本身。1979年威能(Lawrence Weiner)的作品《多個顏色物件併列出所產生一個多顏色物件的行列》(Many Coloured Objects Placed Side by Side to Form a Row of Many Coloured Objects)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19
最重要的是,系列與配置本身並不是真實的,它們僅僅是一種「外像」(image)。20 普宏(Proudhon)曾說:「察覺序列,是為了發現多元整體,以及部分之中的整體性;它不是創造秩序,而是將某個單位放入一個早已整合的顯現之中,藉由其外像召喚出認知。」21 即使我們知道這些序列本身具有任意性與排他性,我們仍會看見以連續性的效果所構成的外像,其實早就是被接受的配置。即便,假設展覽可以接受任何的作品,那它還是遵循民眾任意性,並以此建構起其組織的外像。因此,它並不是真正的「任意」結構,也稱不上幻象,然而, 這個「外像」卻足以讓我們誤以為這是世界的真實運作方式。
隨著時間推移,外像以配置的內化敘事成為人們自說自話、習以為常的故事。當我們面對「外像」,並與其構築的歷史相遇之時,我們就進入了意識形態所編造的敘事之中。普宏(Proudhon)寫道:「人對自然和諧的感性,察覺數量、節奏、變異、時段的變化….從此,他感知到戲劇與史詩。」22 敘事(包含, 戲劇與史詩)正是我們構築自然秩序的方式。換句話說,當「無政府」成為一種個體化的自我表現時,它其實並不再依循序列配置,也無需戲劇或史詩所構成的外像。許多展覽透過創造與服膺一系列的外像來延續其意識形態效果(例如:藝術運動)。即便是最激進、最邊緣,甚至反對主流階級的展覽計畫,即使以「發表」(manifestation)為名,而不是傳統「展覽」,也仍無法擺脫這類的外像架構, 因為它們仍循著影像敘事所引導的老套策略而行動。
仔細思量,任何掌握權力、企圖配置世界秩序的人,必然會反對這些毫無序列、排列、外像、敘事、戲劇、及史詩的「無政府」世界,因為統治者需要這些編排的形式。普宏(Proudhon)曾說:「執政者一定會反對無政府,因為統治者會將『無政府』抹黑為混亂, 並影響到自身的『統治』, 深怕其『權力』無法順利分配及部署。」23 執政者知道:無政府必須被排除在統治之外,一旦蔓延,序列與排列將失去其意義。而策展人都深知展覽中的「序列」的重要性:任何不遵守序列編排的作品,都可能破壞展覽敘事的一致性,甚至動搖策展人自身的權威。「混亂」,不正是策展人最深的恐懼嗎?
V. 趨向「次序」
當然, 「策展次序」極可能複製另一個屬於更大社會脈絡的階級威權的「次序」。24 值得深思的是,這些制度性的問題,其實源於幽靈般的「開端」(archē)。我們更應該準確地提出這個問題:是否存在一種策展方式,能夠避開權威所建構的次序、配置與敘述,並轉向為更為自然的次序,也就是「無政府秩序」?若要回應上述問題,我們必須回到這條「次序」的思路,明辨其可能。
第一,無政府的次序不存在所謂的「開端」(archē)與「終結」(telos);我們不應將「起源」認定為某種「目的」。無政府就是無政府,不需任何外力介入其發生。這就像熱力學的第二定律:它與第一與第三定律並無直接關係。雖然在物理學上,第一與第三定律為第二定律發生的必要條件,例如沒有能量就無法產生混沌狀態。但第二定律本身只是描述次序如何瓦解為混亂,也就是說,它本身就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第一與第三定律至今仍無法證明;若要證明它們,便得先否定第二定律。因此,第一與第三定律就像社會階級與統治的「開端」,它們無法解釋現狀如何發生。25「無政府」作為一種次序,與「外像」邏輯的參照毫無關聯。
我們必須開始意識到「無政府次序」是自然的運動,並且與所有以權力來配置世界的次序方式恰恰相反,無政府的運動拒絕「序列」與「排列」,也反對「外像」的誘惑。對策展而言,這並不表示要反對美術館館長或策展人,而是要質疑其所代表的權威性,反對其單一次序的執念,反對有私人委員會所主導的「序列世界」,進而抵抗各式各樣的外像及敘述,例如藝術家生產、地緣區域、時間斷代、或政治與社會情境所建構的種種分類。
然而,無政府運動根本反對的正是威權與權威,它絕不能被視為是對於法律的「逾越」,或者是對常態、約定俗成、乃至法律的破壞。理由很簡單:任何「逾越」的概念都是建立在某種常態法則之上的。而「無政府」所主張的實踐,則超越了這樣的「逾越」,「無政府」試圖顛覆更為根本層面。換言之,「法律」的存在本身,是依賴於參照一個並不存在的起源, 即「開端」(archē) 本身。正如惹那. 蘇爾曼(Reiner Schürmann)所言:「『無政府』與『逾越』實踐之差異在於其目標:對『逾越主體』而言,是法律;但對於『無政府主體』而言,其所面對的是維持社會整體性的律法。」26 再次強調,「無政府」並不是違法犯罪行徑,而是一種質疑威權基礎的運動,是對社會與文化過度形成的整體性之挑戰。
最後,這個運動本身並不試圖推翻任何專家或專業主義的系統。無政府的目標並非專業;無政府反對的目標是特權、威權與階層制度,而不是針對熱情、執著、貢獻或投入的行動。專家與專業也有可能對特別明顯的配置或排列提出質疑,間接的反對階層性與特權的威權秩序;這些思考包含:「這樣會不會動搖我本身的權利?」「會不會挑戰我代表的群體?」但正因如此,專家或專業人士極為可能提出另一種無政府次序的可能。我的論點涉及兩點:第一,策展應強化與自然次序的對應關係;第二,策展是一種來自於「意願」之間的連結,具有水平結構,體現「動手做」(DIY)的實踐精神。
26 Reiner Schürmann, Tomorrow the Manifold – Essays on Foucault, Anarchy, and the Singularization to Come (Zurich: Diaphanes, 2019), 29. 譯釋:雙括號內為譯者強調。
VI. 自然次序的作用
如同我們在「詞彙」中所述,「自然」自成其自身次序,而我們只需跟隨著自然次序而水到渠成。這當然並不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想像,也不是一種反人類中心的物質唯實論觀點。27 但,如前所述,這意味著自然與社會性、以及無政府嵌合的次序所在。如莫里斯所言:「無政府主義無論在族群或親屬關係的社會中,乃至更複雜社會的日常生活裡,始終被視為一種展現無政府原則的實踐。」28 因此,社會性運作建構在如此的基本信念之上: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並由此組織自己的生命。至少比那種無法溝通的戒律或反覆統治機制更為可取,而這些正是來自長期以來虛偽威權的產物。當外在力量不再強迫時,自然次序與人們的自願次序便能彼此契合。真正的問題在於:當這種作用同時發生於社會與自然之中,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須強調:自然、知覺與文化象徵是密不可分的;將三者分開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知,阻礙了我們對世界處境與角色的真正理解。如果自然不再作為背景,那麼文化與人造物(指:藝術)也無法單獨成為前景。 29 正如莫里斯所說:「作為一個演化的自然主義者,無政府相信世界現實是建立在具體的物質基礎上,伴隨著其傾向、品質、行動,以及與事物之間的關係。生命、知覺與人類的象徵文化,都是由『物』所顯現出來的品質。」30 當象徵文化不再被外在強加為一種系列化的表象時,它與其所伴隨的過度與錯置,其實正是自然次序的一部分,即便它呈現為過度或失序。無政府主義的蘊意在於自然與文化密不可分的永續發展。
我們必須強調:「隨機」與「意外」本身也是自然次序的一部分,因為這種看似常態又具有擾動性的狀態,正是自然本身的樣貌。31「自然次序」絕非僅僅是一團混沌。如莫里斯所說:「雖然隨機與意外是世界存在的本質,但其物質狀態本身絕非混亂。」32隨機與意外實則是人類想像的一部分,是對多樣、變異事件發生的想像。事實上,世界只有一個事件在發生,或將在未來發生。這種應變的場景可能出現在展覽經費的規劃(面向未來),也可能體現於事件的敘事之中,用來賦予偶然事件某種意義(面向過去)。但這些,其實只是可能事件的表象,而這些表象往往錯誤地將人為的因果關係與配置,轉化為一種不可改變的宿命。我們應當再次強調:無論是自然的次序或是無政府狀態,都不應也不能被任何外在的表象所取代,即便那看起來是最隨機、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
讓象徵文化具有意義的方式,不應只是模仿自然,而是必須回到文化驅動力來思考。回應史賓諾莎的概念—「生命驅力」(conatus),也就是每個存在的自我保存意志。33自然在任何時刻都傾向於保存生命,即便面對疾病與死亡;即便是一件藝術作品、一個無生命的影像,或是 AI 般的幻覺,也都可能帶有這股「自我保存」的衝動。正如馬拉特斯塔所說:「人有兩個基本品質:第一、保存自己,沒有這一點,存在便無從談起;第二是保存其所屬類種的動能,倘若無此,類種便不可能產生或持續存在。」34無論我們如何談論社會、社區、機制與物件,它們都包含這種「生命驅力」的聚集, 同時也是「保存自身」的自然傾向。
然而此刻,人類的「生命驅力」正對抗自然, 並與之衝突。這意味著人類正與自己為敵,雖然這樣的認知令人悲傷,卻又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的裙帶關係所構成之世界,以外部的序列、預設的配置、協作的圖表與預期利潤進行全面的操縱。如馬拉特斯塔所言:「在自然中,生命可以透過兩種方式來維持自身與其愉悅:一是與同類或異類的抗爭,二是互相的支持與合作;沒有後者,沒有任何一種族類能夠被形成或持續存在。」35若要增強我們的生命驅力,並使其與社會性發生實質作用,我們更需倚賴後者,也就是互助與共生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讓單一個體得以延續,也讓所有族類、所有生命形式在此基礎上得以凸顯自身,而非走向滅絕。至此,「無政府—自然—文化—次序」之間的作用關係,已勾勒出一幅可辨識的藍圖,讓我們再回到策展這個命題上。
VII. 無政府策展
何謂「無政府策展」自然次序化的運作範式?莫里斯寫道:「創造一個共有的社會、自我組織與自下而上的民主,以形塑不以利潤為目的的生產,這些對無政府是重要的。」第一個困難是如何分辨需要(need)與利潤。從史賓諾莎的觀點來看,答案總是依賴於目的,但自然當然不需特定目的,那只是預先控制未來的外在表象。36 策展可以先評估其需求,而不以利潤為最終目標(也不以外部參考價值的貨幣為導向),轉而發現多重連結的交換網絡;37 重點在於強調社會價值並非以生產「外像」為導向,並尋找任何可行方式決定連結路徑。我們需要資金提供者支持永續經營,而不要求可回收的自由,策展的社會性是自然的供需關係所調節的參與者之利益。
第二個困難, 是自我管理的難題。我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實踐必須採取多元而靈活的策略,隨著人的需求與自然法則而調整。如莫里斯(Morris)所言:「無政府主義倡導政治策略的複數性,特別針對差異化的社會歷史處境,以及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性。」38 這樣的觀點並非預設一種固定的自我組織模式,僅作為「生命驅力」改善的機制,而是強調政治實踐的多樣性,透過志願性組織,讓所有參與者都能平等發聲。策展在此脈絡下,不僅要確保工作的自主性與彈性,更應尊重主體間的差異與複數性,讓各種能力與聲音共同平等參與、相互交織,進而實現一種開放於所有人的普世福祉。
第三個困難:「水平式民主」(horizontal democracy)計劃的有效運作,並防止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然而,現實中統治者往往藉由實質性的權力工具「無論是知識、制度,或是經濟力量,使每個人被動地實踐統治掌權者的意志。」39 面對這種狀況,無政府主義與秩序的關係,必須建立在互助合作的原則上,透過去中心化與多元策略的方式避免權力核心化的形成。對於策展而言,這種實踐意味著展覽任務之間的連結不應建立在專業知識的階層之上,而應促進技術的共享、平等的付出、輪班的責任制、非托管式的協作,以及離群卻共作的工作形式。如果藝術家仍在世的話,讓藝術家參與策展決策。這是平行且水平的操作方式,遠比階層式的垂直體系來得更為開放與公平。
最後,無論威權如何控管,集體的生命驅力始終與社會性共同運作。這當然並非一開始就是自明的。如馬拉克斯塔所言:「讓所有人能夠結合為團結陣線的是『無意識』,因為『無意識』能自發地從特定利益間的摩擦中浮現,當人們立足於自身位置,而非走向抽象的『一般利益』時,正是團結陣線作為人類生活自然法則的最佳證明。」40 集體的自信始終是推動的力量,它既非抽象,也非一般性的利益。那麼,當策動一個組織或展覽時,我們是否更應該關注成員的利益,而不是僅以單一面向操作對「一般觀眾」的想像?這樣的實踐無須個人層面的操作,而是強調與「自然法則」的協作;能「零風險」地實現共享集體利益。
如果我們把這一切攤開來共同思考,就會理解「無政府式策展」就會理解,「無政府式策展」是一種結合合作、水平性、團結陣線與自然的實踐。這並非遙不可及。正如馬拉特斯塔所說:「無政府並非完美,也不是一種絕對的概念;它就像地平線,當我們走近它時,便向後退去。『無政府』是一條通往更好的開放之路。」41 因此,無政府次序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態,也不是一種不可實現的理想主義承諾——這兩者都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模式。就如同自然的次序,無政府與策展都不是完美的模型,是一種多元策略與平等聲音共同實踐的開放進程,體現了每一位成員生命意志的展現。因此,並不存在一套方法學架構可供遵循,也無法透過教條式的方式加以複製。無政府策展是一場針對問題的集體共同研究,是群體開發與探究的陪伴歷程;正如楊硯奇所說,它更像是「一團互相纏繞的線條」42——絕不是由某位周遊列國的策展人跟團隊定義「這團線」之意義。
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幾乎一切都服膺於階級與威權的體系,被競爭與對抗所主導。然而,如先前所述,無政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自然的允諾,也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它代表著對階級與威權的拒絕。我們不妨再次引用巴特比(Bartleby)的名言:「我寧可不要。」43 正如無政府主義者傑夫・商茲(Jeff Shantz)所說:「為了將理念實踐於生活,無政府主義以生活為場域,進行各種實驗;這正是我們所說的DIY精神——透過對『共識』的拒絕,轉而實踐其他形式的契約與關係。」44 對策展而言,這樣的思想意味著我們必須從拒絕共識開始,反思策展是否一定只能透過那種垂直結構與資本合作才能展開?我會說:「我寧可不要。」去中心化的溝通與交換,是否可能不以犧牲自由與便利為代價?答案是肯定的, 必須堅持著有如驢子般的執著——那是延緩寡占權力速度的實踐。
「動手做」(DIY)是一種可行的行動策略,如商茲(Shantz)所言,「『動手做』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歷史,並深植於無政府主義的實踐之中。我們可以從朴紅的『人民銀行』與另類貨幣制度看出這一脈絡,也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北美班雅明・塔克(Benjamin Tucker)的無政府社區所實施的『以物易物系統』(LETs), 這符合了當代的『自主地帶』(autonomous zone),也延伸至今日的『佔屋社群』(squat community)。近年來,情境主義(situationist)、紅帽子(Kabouters)與英國龐克運動亦倡導以『動手做』為基礎的行動主義,以因應流動化的消費時間制度,及被權力與控制結構宰制的工作關係。」45 這樣的實踐在文化領域中也極為鮮明,成為一種反向的藝術策略,從達達主義的甘恩(Aleksei Gan)到崔斯坦(Tristan Tzara),再到最近的無政府藝術實驗,構成一條多樣而激進的創作系譜。值得一提的是玻利維亞的「女人創造」(Mujeres Creando, https://mujerescreando.org/)藝術團體,他們自1992年起展開一系列不以階層或政治目的為導向的平等合作,包括街頭表演、佔領街道、人民集會、塗鴉與抗議行動,以抵抗右翼、父權體制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展現出「動手做」DIY策略在藝術與社會實踐交織出的另類可能。46
還有許多值得提出的例子,讓我們能夠在階層體制之外,探索新的社群關係與非特權式的權力模式。正如商茲(Shantz)所寫:「這些行動也包含無領導者的小型團體,透過激進女性主義、公社式合作、療養實踐、學習網絡、媒體團隊與直接行動,持續對災難、罷工、革命等…緊急狀態做出回應。」47 這些自發性的組織實踐,例如社群自主管理的托育中心、地方性組織、或是知名、具行動力的工會團體;雖然,他們不是嚴格定義下的無政府組織,卻展現出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精神與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這些組織對於公共空間極為關鍵。沒有這些自發的社群組織,就沒有真正的社會性。48 策展人(或藝術家)如果真要強化社會性、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那其中所蘊藏的可能性,將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必須明白:尤其當我們必須一切從頭做起,實驗是必要的過程, 而「追求完美」恰是無政府實踐的反面。
VIII. 結論
那我們現在還能做什麼呢?從最廣泛的角度來說,就是讓「開端」和「終結」不再只是權力架構以及意識形態的配置與調整,將其作為過時的歷史。由此,將「開始」和「結束」交給不斷變動的「在地抉擇」(local determination)。今天的世界持續陷入戰爭與衝突,是因為那套早已過時的階層制度違背了自然運行以及生命驅力。那些暴君、獨裁者、極權領袖與寡頭們,當他們聯手控制世界時,反而讓整個人類走向毀滅,這是因為他們的無能,讓人們無法與自然共處,無法與「無政府」共處。所以,「我們還能做的」, 正是學會拒絕對階層制度的盲目服從和跪拜。 過時的權力結構,往往無視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只為了鞏固自己的位置,阻礙所有人的權利實現。當然,改變是不容易,因為有害怨恨會全面壓制改變的發生;但是,在這個不斷生滅的浩瀚宇宙中,當「改變」開始變得可能的時刻, 我們就須把握這唯一的機會。
這個答案同樣適用於無政府:讓「開端」(archē)與「終結」(telos)不再受限於既有權力的結構與僵化的歷史想像,而是視為過往的經驗,交由不斷變動的策展「在地抉擇」。重點不在於延續某些過往的階層制所建構出的權力系統,也不是去堅持「這是藝術所配置的世界狀態」或「這是某位策展人所定義的普世歷史」等特定陳述——其實這些僅僅是違背自然法則與人性條件的想像配置罷了。真正的「無政府策展」應該回歸自然原則,讓策展回到社會性的起點。也許最困難的任務,就是開始學會說話「我寧可不要….」,學會把集體的權力放在個人意志之前,學會優先考慮社會的福祉,而不是複製威權的藝術語言與展示形式。那麼這樣,藝術世界會因此變得更好嗎?或許無法立刻回答,但我們可以確信:當我們把自然與文化視為一種共時共享的存在,而非某個個人可以主宰的末世論敘事,我們就已經打開了通往新的策展實踐之路徑。那就是一種無政府、水平開放、DIY的策展行動——讓所有實踐都能回應各自的需要,並與在地需要與互利連結在一起。
如果執行長、營運長、藝術總監與策展人能夠放下其特權教育與優勢背景,關注手下工作的人,差異的策展方式將會發生。如果「社群團結」被視為策展的本質起點,那麼傾聽那些在決策之外,卻默默從事機構日常工作的人員——包括負責清潔、維修、守衛、監看與整理等等的——就變得格外重要。沒有發言權的聲音更應該納入策展之中。只有當他們從一開始就參與到展覽內容的各個層面,策展才有可能走上一條真正的「差異之路」。也唯有如此,策展中的「序列與配置」,才能接受質疑、擺脫並鬆動單一主導。「平行式策展」不是一種折衷方案,而是能為社群帶來真正良善秩序的方法。這樣的策展實踐,不再是由上而下的敘述,而是共同參與、共同照料的敘事重構。所謂「無政府策展」,並不是混亂或放任,而是邁向與自然共融的初始,是不模仿中心、不服從權威、堅持共榮共存的策展秩序。
那麼,我們到底還需不需要策展人?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這份工作不再被視為一種擁有特權的位置,而是一種可平行移轉的技術角色。策展專業長久以來執迷於詮釋與敘述的權力,把自己定位成作品的解釋者與文化秩序的制定者。然而,在當前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當下,策展正面臨威脅,且被低估輕忽;也許, 策展是目前最容易被人工智慧取代的文化職業之一。那麼,有什麼能夠拯救「策展人」這個角色?一種解決的方案,是選擇是訴諸情感與直覺(也就是AI無法模擬的部分),但是這條路可能再次陷入「有品味」、「有慧眼」的老路。另一種方法,則是發展一種與「自然」深層協作的策展行動,實踐一種可移轉、可共享、去中心化的權力技術架構。如果策展人願意走這條路,他們或許就能從人工智慧的陰影中轉身而出,成為重新調整世界秩序的行動者——不是因為他們坐享特權,而是因為他們願意放下特權,實踐真正「無政府式」的策展工作。
如前所述,無政府狀態是一條開闊的道路。正如舒爾曼(Schürmann)所說:「與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相比,今日的無政府主義可能更加貧瘠與脆弱。它不再依賴線性的歷史敘述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而僅剩歷史的主體性,然而此一主體早已中斷。」即使有所逾越,主體依然難以擺脫對法律的拜物心態,而這種逾越本身也反覆地與禁令對抗。在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中找到「無政府主體」的回音:「這就是我的道路;但你的路在哪裏?單一、普世的路不會存在。」49 尼采睿智警句的揭示: 我們不能為「還能做什麼?」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因為有著各式各樣的策略可以防範階級與權威繼續毀壞我們的生活。但,「無政府策展」的因應策略,是我們當下唯一可行的決擇,舒爾曼提醒過我們:「沒有『應該』這回事。」50 我們當然不能從理論或歷史邏輯中產生某個「應該」方案。然而,這篇簡短札記記載了我試圖穿越籠罩在「視閾」陰霾下進行的思辨。那麼,屬於「你」的那條「路」,會從何處開始呢?51
1 「過剩」(excess),帶有「剩餘」,也指超越已知之物。參照社會學家的觀點,「象徵文化」(symbolic culture)應理解為那些經由大眾媒體的操作、成為集體信仰的事物。
2 See Michael Bhaskar, Curation: The Power of Selection in a World of Excess (London: Piatkus, 2017), 7-8. 譯釋:雙括號內為譯者強調。
3 譯註: order 有次序、戒令、 管理、命令等意涵。 在本文中這個字出現時, 利用雙關語方式「次序/ 命令」 呈現。
4 關於列寧所提出的問題「還能怎麼辦」也暗示著思想的枯竭,可參閱 Althusser、Badiou、Gauchet 與 Nancy 的著作,同時也可參考 Susan Kelly 的研究: Susan Kelly, “‘What is to be Done?’ Grammars of Organisation,” Deleuze and Guattari Studies 12, no. 2 (2018): 147-84.
5 在藝術的部分,參考 Josh MacPhee and Erik Reuland, eds. Realizing the Impossible: Art Against Authority (Chico: AK Press, 2007); Allan Antliff, Anarchy and Art (Vancouver: Arsenal Pulp, 2007) and Michael Paraskos, Four essays on Art and Anarchism (Mitcham: Orage Press, 2015).
6 Baruch Spinoza, Complete Works, trans. Samuel Shi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2), EIVP4Pr., EIP23Pr., TPT§3:45, EIIP29Cor., TEI§84. 這裡所涉及的是一種「被造自然」(nature natured),也就是既非我們所建構的想像世界觀(那是一連串的配置與結構,參見第4節),也不是「自然的自我生成」(nature naturing),對人類而言這是不可掌握的。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在此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7 Spinoza, Complete Works, EIP33Sch.2.
8 Brian Morris, A Defence of Anarchist Communism (London: Freedom Press, 2022), 101-2.
9 如貝勒加里格(Bellegarrigue)所說:「自然狀態已經是社會狀態;因此,企圖用一紙契約去強加一個本已存在的狀態,不只是荒謬,甚至可以說是猥褻的。」 Anselme Bellegarrigue, Manifeste de l’anarchie [1850] (Montréal: Lux Éditeur, 2022), 32, 作者自譯。
10 Enrico Malatesta, Anarchy, trans. Vernon Richards (London: Freedom Press, 2009), 40.
11 Malatesta, Anarchy, 4.
12 Benjamin Tucker, Instead of a Book (New York: Tucker Publishing, 1897), 14.
13 Bellegarrigue, Manifeste de l’anarchie, 1, 作者自譯。
14 常識的危險性,見 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trans. Joseph A. Buttigie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24-707.
15 如貝勒加里格(Bellegarrigue)所說:「從神權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不可能僅僅依靠選票權,因為這樣的權利只是用來防止政府滅亡,也就是說,用來維持政府優先性的原則。Bellegarrigue, Manifeste de l’anarchie, 19, 作者翻譯。
16 Pierre-Joseph Proudhon,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Garnier, 1851), 144, 作者自譯。 譯釋:雙括號內為譯者強調。
17 國家與美術館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 See, amongst other, Didier Maleuvre, Museum Memo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 Pierre-Joseph Proudhon, De la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 (Paris: De Prévot, 1843), 1, 作者自譯。
19 寓言( allegory)的概念, 參考 Jorge Luis Borges, “The Library of Babel,” trans. James E. Irby, in Labyrinths (London: Penguin, 2000), 78-86.
20 文中「image」有著政治哲學的考量,一方面有著西方哲學有關擬像的思考, 另一方面, 有著情境主義的奇觀spectacle 的意義, 更有著「外表」(appearance)及「本質」(essence)的辯證意義。 在翻譯中, 統一將image 翻譯為「外像」。
21 Proudhon, De la création, 212, 作者自譯。
22 Proudhon, De la création, 135-6, 作者自譯。
23 Pierre-Joseph Proudhon, 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 (Paris: La Voix du peuple, 1849), 46, 作者自譯。譯釋:雙括號內為譯者強調。
24 這類的論述請參考 Peter Aronsson and Gabriella Elgenius, eds., National Museums 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1750-2010 (London : Routledge, 2015).
25 這個命題可參考 Eric Johnson, Anxiety and the Equation: Understanding Boltzmann’s Entropy (Cambridge: MIT Press, 2018).
26 Reiner Schürmann, Tomorrow the Manifold – Essays on Foucault, Anarchy, and the Singularization to Come (Zurich: Diaphanes, 2019), 29. 譯釋:雙括號內為譯者強調。
27 新物質主義似乎對無政府有所保留,或許是因為其「穿越-互動的能動性」(intra-active agentism)仍依附於某種特權性的、因而是階層化的、以邏各斯中心(logocentric)為基礎的表述邏輯。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在此深入討論這個主題,以及它與斯賓諾莎主義的比較。 參考Karen Barad, Jane Bennett, Elizabeth Grosz, Rosi Braidotti, Vicki Kirby, amongst others.
28 Morris, A Defence, 17.
29 這個主題請參考 Vicki Kirby, ed., What if Culture was Nature all Alo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30 Morris, A Defence, 19. 雙括號為譯者所強調
31 Spinoza, Complete Works, EIIP44Cor.1, Letter #54.
32 Morris, A Defence, 94.
33 Spinoza, Complete Works, EIIIP6, EIIIP7Pr, EIIIP59Sch.
34 Malatesta, Anarchy, 8.
35 Malatesta, Anarchy, 15.
36 Spinoza, Complete Works, EIVP52Sch.
37 就像「開端」(arché)與「終結」(telos)一樣,金錢是另一個被排除的參照物,卻規範著所有經濟與社會的交換行為。See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Edward Aveling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2003), 79. 有關資本主義之外的價值理論, 見 Brian Massumi, 99 Theses on the Revaluation of Val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and with regards to curating, see Hongjohn Lin, “The Economy of Curation and the Capital of Attention,” Curatography 13 (2025), https://curatography.org/13-0-en
38 Morris, A Defence, 128.
39 Malatesta, Anarchy, 7.
40 Malatesta, Anarchy, 21.
41 Malatesta, Anarchy, 37. 譯釋:雙括號內為譯者強調。
42 Yenchi Yang, “In Praise of Troubleness,” Curatography 13 (2025), https://curatography.org/13-3-en
43 Herman Melville, Bartleby, The Scrivener: A Story of Wall Street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1856), 201. See also Giorgio Agamben, “Bartleby, or On Contingency,” in Potenti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3-71.
44 Jeff Shantz, “Anarchy Is Order: Creating the New World in the Shell of the Old,” Media/Culture Journal 7, no. 6, unpaginated, https://doi.org/10.5204/mcj.2480.
45 Shantz, “Anarchy Is Order.”
46 更為複雜的觀點, 參考 Maria Galindo, Feminismo Urgente: A Despatriarcar (Buenos Aires: Lavaca, 2022)
47 Shantz, “Anarchy Is Order.”
48 我在這裡特別想到的是「奪回街道(或海灘)」運動,以及藝術家創造的綠地空間,例如艾格妮絲・丹妮絲(Agnes Denes)、梅爾・欽(Mel Chin)等和游擊園藝行動。
49 譯釋: 換言之, 自己必須走自己的路。 Schürmann, Tomorrow the Manifold, 29. For Nietzsche’s quote, see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6.
50 Schürmann, Tomorrow the Manifold, 29. 譯釋:雙括號內為譯者強調。
51 感謝斯德哥爾摩大學(University of Stockholm)的 Magdalena Holdar 和 Daniel Siedell 所提供的回饋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