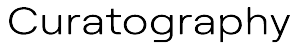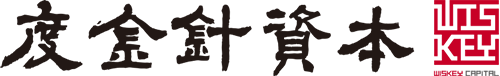一天早上,我讀到了東京森美術館「機器之愛:電玩、人工智慧與當代藝術」(Machine Love: Video Game, AI and Contemporary Art)展覽的展訊。這個展覽的展名使我立即想到了格諾斯可(Gary Genosko)和黑崔克(Jay Hetrick)十年前所編的瓜達希的日本書寫的論文集《機械愛慾:日本書寫》(Machinic Eros: Writings on Japan)。無創造力掌控著一切。與其積極且帶有創造力地診斷我們的全球社會的基本結構,並試圖尋找模控或逐漸改變現狀所需的藝術作品和展覽,現在處理當代藝術於「人工智慧、人類世或地緣政治衝突」中的角色的書的最後幾頁只敢提及藝術的「想像」(imaginative)功能。面對「AI的過度進化、人類世和地緣政治衝突」所帶來的危機,我們今日見證的是當代藝術世界的貧乏、保守甚至退縮的論證。
AI、人類世和地緣政治衝突時代的藝術
事實上,當代藝術世界大部分的書都僅處理上述的其中一個危機。很少有當代藝術世界中的書籍處理上述的其中兩個危機,而令人遺憾地,根本沒有書籍以當代藝術的方式同時處理上述這三項危機。1 舉例來說,黑瑟.戴維斯(Heather Davis)和艾提安內.特坪(Etienne Turpin)在他們所編的《人類世中的藝術:美學、政治、環境和認識論的遭逢》一書中,在進行「超越地質學的外推」、討論「感性」和「知覺」、標示「受爭議的領地」,並「沉思世界的倖存」後,將他們的導論的最後一部份命名為「值得想像的未來」。2 吉歐萬尼.阿羅伊(Giovanni Aloi),在其《思辨式的動物標本剝製術:自然史、動物表面與人類世中的藝術》中,在探索「動物標本剝製術的表面」、「自然史全景敞視監獄」、「動物可見性」,而忽略了人與動物間互連的現實複雜性與科學/資本主義光學的多面向性之後,最終僅揭示了撫慰與得以創生知覺和同情的「象徵性想像」。珍.雅戈辛斯基(Jan Jogodzinski),在其《質問人類世:生態學、美學、教育法與打上問號的未來》一書中,尷尬地顯示的是夾在同調的(homological)「媒體與藝術回應」和毫無準備的「資本主義框架」中的「想像物」。3 蘇珊.巴拉德(Susan Ballard),在其巨作《人類世中的藝術與自然:行星美學》中,在將「全新世」(Holocene)、人類世和「資本主義加速」給詩意化之前,提及的則是藝術作品的「做工」、可見化,且因而是「想像」力量。4 薩奧馬.莫拿尼(Salma Monani),在其《人類世的電影:情感、生態學與比人類更多的親屬關係》一書中,將其前言的主要標題命名為「為了做夢被創造」(Created to Dream)。5 同樣地,在這本書的導言中,卡塔奇娜.帕茲奇維茲(Katarzyna Paszkiewicz)也提到了這本書的主要目標是去挑戰我們的「自然排除」(natural exclusion)的二分,並藉此使我們「意識到」我們在自然中的角色。6 比爾.吉爾伯特(Bill Gilbert)與阿尼卡.考克斯(Anicca Cox),在《人類世的藝術策劃:社群和環境中的藝術》一書中,提出了「邊際烏托邦」(utopia of the edge)的論點,其主要目標在於維繫不論如何的鄉村和城市烏托邦理想的「想像性後果」(imaginative aftermaths)。7
而《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一書的作者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與艾蓮內.岡(Elaine Gan)、黑瑟.史旺森(Heather Swanson)和尼爾斯.布班特(Nils Bubandt)一道,呼籲我們應重視「石頭的幽靈輪廓、指紋的放射性、鱟的卵、野生蝙蝠傳粉者、草地上消失的野花、墓碑上的地衣、生長在廢棄汽車輪胎裡的西紅柿」的「駭人地景」中的「想像力」。8 珍妮佛.菲伊(Jennifer Fay),在她的《無庇護的世界:人類世時代的電影》一書中,提出了「人造世界製作」,因而是電影在人類世時代的「影像製作」能力的論題。9 卡亞.巴瑞(Kaya Barry)與鍾迪.奇安(Jondi Keane),於《人類世的創意手段:藝術、機動性和參與式地理學》中,提倡並期待的是藝術創作過程的「想像力地領導」(imaginatively leading)力量。10 茱莉.萊斯(Julie Reiss),在其所編之《人類世中的藝術、理論和實踐》一書的前言中,提倡了作為當今最重要任務的「藝術有助於我們想像另外的世界與可能的未來的潛能」的這件事。T. J. 德莫斯(T. J. Demos),在其《超越世界的終結:在十字路口的生活藝術》一書中,在對當代的死亡政治、媒介生態學、地理工程、鬼魂、視覺政治、動物宇宙政治和「激進的系統性變革」進行研究前,開啟的是得以使我們「重新想像世界」的「裂域」(rift zone)競技場。11 最後,崔維斯.何洛威(Travis Holloway),在其《如何在世界盡頭生存:人類世的理論、藝術和政治》一書中,在提倡「反歷史」(counterhistory)、「從後現代藝術到人類世的轉變」和「世界盡頭的民主」進行倡導前,抽象,且無意義地論證了我們應該發明和想像「動物生命統治」(zoocracy),即一種權能(kratos),或一種生命對自身的治理的這點。12
繪製數位技術獨體化結構圖的重要
在這些思想家已知的取徑內,似乎我們對「人工智慧、人類世或的地緣政治衝突時代」的個體結構早已有一個共識性的視野。更有甚者,我們更持續地生產出那麼多「有所本」(based-on)的書、畫冊、傳單和展覽。事實上,我們對我們自身的基本獨體化結構,對這個全球社會的基本結構根本一無所知。而沒有對這個基本結構的認識,根本沒有書、畫冊、傳單、展覽(的效力)能夠被設想和評估,就別說真的製作或操作(making)它們了。
據法國哲學家貝爾納.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及其學生許煜(Yuk Hui)所說,我們當今所承受的是所謂的「去獨體化」(disindividuation)的過程。13 會有這種判斷是一種文化抽象化和異化的結果,某種史蒂格勒與許煜都景仰的法國哲學家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所極力反對的抽象化和異化。事實上,我們現今所承受的是數位技術獨體化(digital technical individuation);透過這種數位技術獨體化,我們才得以進行獨體化,並以一種數位技術的方式與他人區別(differentiate)開來。這個數位技術獨體化形成了使主觀化(subjectivation)和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得以在其上升起的吾人日常生活最根本的軌道。我們能借鑒從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那裡的《空間物構成的手稿—從D手稿》,特別是其中收錄的胡塞爾於1917和1918年寫的〈幻物的多重相關性。正常與不正常運作的身體〉一文中抽取出的「線的理論」(theory of line)繪製這種數位技術獨體化的結構圖。14
當今真正的獨體化的佚失
無論如何,當今沒有理論家、哲學家、策展人曾論及這種數位技術獨體化,更別說繪製任何結構圖了。這就好像數位技術獨體化根本不存在,且我們所擁有的只有成功或失敗的主觀化和/或主體化罷了。我們在現今當紅的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書寫裡可看到這點,其書寫代表的是對獨體化的遺忘。我們在史蒂格勒的書裡也可以看到這點,其反映的是單調的獨體化。我們在許煜的著作中也可發現這點,其呈現給我們的是某種獨體化的錯亂。我們也可在法蘭柯.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的分析和診斷中看到這點,其再現了獨體化的錯置。最後,我們在班雅明.布萊頓(Benjamin H. Bratton)的書中也可讀到這點,其顯示了對獨體化的誤識和固化。就連聰明和傑出的藝術家暨理論家希朵.史特耶(Hito Steyerl),於其新書《媒介熱:熱浪時代的影像》中,都錯失了我們,包括那些掌控著我們的生活的工程師、CEO和股東們全都深陷其中的「無論如何的韋伯式的鐵籠」(whatever Weberian iron cage)。

2 Heather Davis & Etienne Turpin, Art in the Anthropocene: Encounters Among Aesthetics, Politics, Environments and Epistemologie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5), p. 20.
3 Jan Jogodzinski, The Interrogating the Anthropocene: Ecology, Aesthetics, Pedagogy, and the Future in Ques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xiii-xv.
5 Katarzyna Paszkiewicz & Andrea Ruthven (eds.), Cinema of/for The Anthropocene: Affect, Ecology, and More-than-Human Kinship (London: Routledge, 2025), p. xi.
8 Anna Lowenhaupt Tsing,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of the Anthropoce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p. 12.
9 Jennifer Fay, Inhospitable Worlds: Cinema in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20.
10 Kaya Barry & Jondi Keane, Creative Measures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Mobilities, and Participatory Geographies (London: Palgrave Mcmillan, 2019), p. 1-24.
12 Travis Holloway, How to Liv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ory, Art, and Politics for the Anthropoce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14.
將批判點多元化
所以,策展還能做什麼?不論是在絞盡腦汁地豐富,或令人遺憾地缺乏的意義,不論是在日常對話的語境,或是在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雪尼謝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列寧(Vladimir Lenin)、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巴迪烏(Alain Badiou)和儂希(Jean-Luc Nancy)專屬的意義上,「策展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都在於對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乃至於這個世界進行診斷,去繪製這個社會或世界的結構圖式,並以策展實踐去模控或改變它的這點。換句話說,這也意味著去繪製我們的數位技術獨體化(digital technical individuation)的結構圖式,使我們自身重新導向,並因而以策展實踐模控或改變我們自身。或者,再換個方式說,這也意味著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將法國哲學家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所說的「批判點」(critical points)多元化,也就是,將我們向當代藝術之地拖,並使我們心中的那些叢生的心智線交錯,形成在我們共享的這個資本共產主義時代(舉例來說,當我們拿出我們的智慧型手機與我們的朋友們或其他人一起尋找和分享最佳的用餐地點之時彰顯的就是這樣的時代),形成與在作品前拍照、後退、曝光、欣賞和跨獨體化時,無意識或部分意識地形塑之前個體之真實點相呼應,或得以取代這些前個體真實之點的非常不同的批判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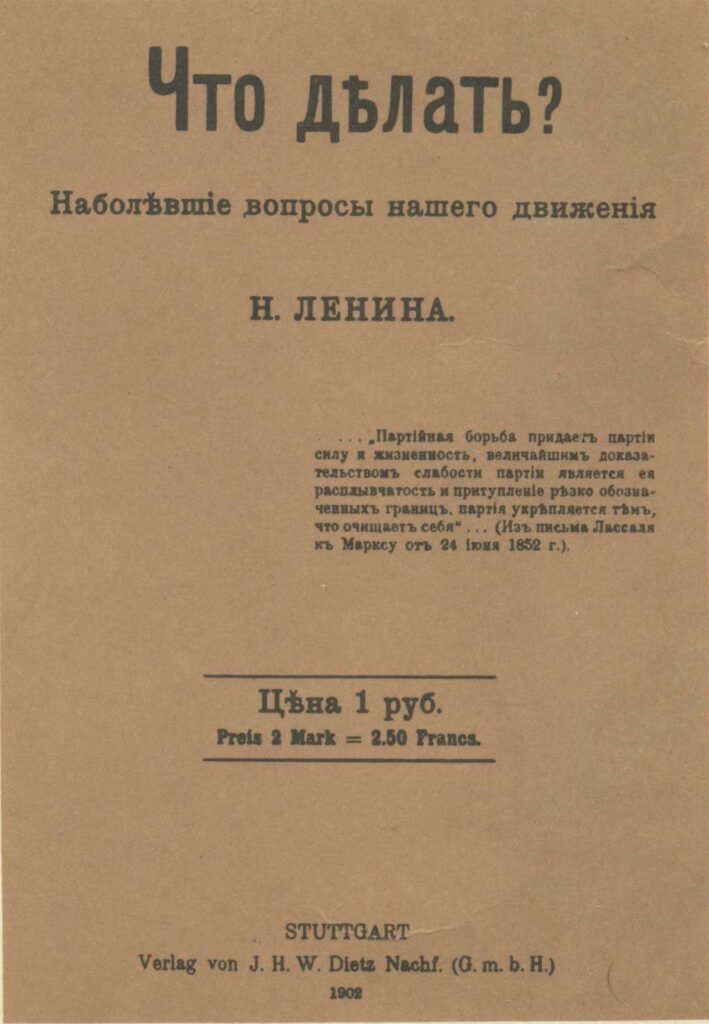
「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的譜系
對西蒙東來說,批判點是每種不同類型的獨體化的目標或理想之點。批判點是獨體化的「加一」(plus one)。從雪尼謝夫斯基1863年的社會公社導向的烏托邦理想、列寧於1901和1902年對布爾什維克政黨(Bolshevik Party)建立的迫切想望、阿圖塞於1978年的歷史主義和意識形態式的支持、巴迪烏和勾謝(Marcel Gauchet)於2014年的對共產主義的再理念化,到儂希於2016年對這個問題進行的非運作、無目標、漫遊和被曝在於外的再位移;這些對「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進行的回答全都見證了如此熱切的批判點之精神,以及如此不可能,但必要且永不傾倒的共產主義。
事實上,作為政治,甚至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問題的「還能做什麼?」的這個問題是從俄國哲學家暨作家雪尼謝夫斯基1863年的小說《還能做什麼?》出現的。雪尼謝夫斯基的這本小說回應的是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62年的小說《父與子》。雪尼謝夫斯基的這本小說描繪了主人翁維耶拉(Viéra)看似失敗,最終實則成功的社會主義公社實驗,以及與職業和自由選擇有關的突破。它揭示了兩對對美國充滿著仇恨,且有著社會主義傾向的伴侶的「快樂結局」(happy ending)。這個「快樂結局」啟發了列寧,使其於1901和1902年寫下了同名的長文〈還能做什麼?〉。從對於「批評」的狀況、「批評的自由」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對「理論鬥爭」(theoretical struggle)的檢視開始,列寧著手於文中將「群眾的自發性」與「社會民主意識」理論化。15 在與「毀謗份子」和「神秘份子」對抗的情況下,列寧將勞動階級標舉為「民主的冠軍」,且最重要之事乃是對布爾什維克政黨,也就是共產黨的「充滿尊嚴」(respectful)的復興的迫切性。16
之後,在二十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也以同名文章回應了這個問題。從政治路線相對於黨路線的優先性出發,阿圖塞強調對勞動階級鬥爭進行政治分析的重要性,這樣的重要性,如同阿圖塞自己所說,「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或知識狀況的政治意識」等同。除此之外,阿圖塞也擁護地指出,工人的機動性應該也將會依資本的機動性改變。對大量生產的資本主義體系之機制的「具體分析」(concrete analysis)必須被維持,且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歷史性格」(historical character)也應該被追溯。17 這就是阿圖塞對「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的回答。在與法國歷史學家馬塞爾.勾謝(Marcel Gauchet)進行同名對話的情況下,法國哲學家巴迪烏,在描述其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後,提倡了馬克思的叛變主義(insurrectionism)和列寧的「模糊性」(obscurity)。18 換言之,在共產主義作為資本主義邪惡的救星、不自然地以國家為中心、分工傾向的理念的基礎上,給出所謂的實驗性的「共產主義假設」,也就是說,將「共產主義理念」付諸實驗性實踐與對未來可能性的投射乃是必要的。19 維持共產主義假設和共產主義理念總是可能的。這就是巴迪烏對「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的回答。最後,法國哲學家尚-呂克.儂希,在申明這個問題的「重塑」的必要性的之後,在同名的書中指出了康德(Immanuel Kant)、胡塞爾、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其他哲學家都曾以他們的方式回應過這個問題。而雖然是對這個問題進行之不同位移,儂希認為,在哲學史上對這個問題進行過的不同回應實是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的真正「開始」(beginning),根據「內心圖像的改變」之於真實的「改變」或「改造」(making; faire)的優先性。還能做什麼?儂希,作為一位解構主義哲學家,提出了非客體、非計畫性、非成效性的「曝露於無限」,或「對存在相對於無限的展曝的肯認」,也就是說,策蘭式的(Celanian)的「沒有岸畔的作業」(make without shore; faire sans rivages)才是我們應將其視為「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即「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的可能性條件之物。
能源弱者聯盟與休停式策展
因此,假如「策展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面對的是「人工智慧、人類世或地緣政治衝突的時代」呢?答案也很清楚地是一樣的。我們,作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人類,正以技術地跨獨體化,或甚至數位地和技術地跨獨體化著自身的方式形塑這個時代活生生的真實。事實上,我們的數位技術獨體化加速地越快,受科技戰爭、人類世和地緣政治衝突所侵害的群體所受的戕害就越劇烈。稀有的自然資源和貴金屬主要產於全球南方。真正的平等才是我們必須努力之處。或許,為了讓這個使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時代變得垂直和不平等的「無論什麼機器」(whatever machine)休停,為了在現在,回答「策展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與其採取拉圖式(Latourian)的「重設」(reset),一個「能源弱者聯盟」(Coalition Of Resourceful Weaks, CORW)與「休停的美學」(shut-down aesthetics)、「休停的藝術」(shut-down art)和「休停式策展」(shut-down curating)是需要的。
有鑑於此,我們很榮幸,也很高興地邀請了三位作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意義深遠地深刻的探討。透過對巴斯卡、普魯東、史賓諾莎和其餘哲學家論述的運用,尚-保羅.馬提儂(Jean-Paul Martinon)在他的文章中鑄造了「策展無政府狀態」(curatorial anarchy)這個概念,並指出唯有透過這種水平、無領袖、平由(equaliberal)式的方法,我們才能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回應「策展還能做什麼?」的問題,以及面對上述的危機。透過反思性地回溯其先前的駐村經驗,呂岱如(Esther Lu Dai-Ru)細細地透過她是如何被緩慢、平和與平等的非人物種、非人類中心,且從「呼吸」和「演化」匍匐而出的「深時思維」的「共成」和「酷兒曲線」所打動的方式啟發了我們。最後,李泳麒,透過敘述他在將「瓷相」(porcelain photos)或「相瓷」(photoceramics)視為「行動美術館」(mobile museum)的藝術計畫的路上的遭逢過程,追索了香港的「瓷相」或「相瓷」,並點出了與日常攝影、相片人造物,以及與「策展還能做什麼?」這個問題有關的攝影實踐上的平等的重要性。在面對上述的危機時,策展者專業也將變成某種水平和平等,且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專注於其上的「自我技術」(technics of the self)。而這也許將是對「策展在今天還能做什麼?」這個我們,作為當代藝術的從業者,永遠應該問的問題所進行的最好回答。
1 我們看到許煜,以一種非當代藝術的方式,特例地在《機器與主權:為了一種行星思維》(Machine and Sovereignty: For A Planetary Thinking)一書中嘗試去處理上述的三個危機,雖然以一種「已知」(given),也因此是「無意義」(meaningless)的方式。
2 Heather Davis & Etienne Turpin, Art in the Anthropocene: Encounters Among Aesthetics, Politics, Environments and Epistemologie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5), p. 20.
3 Jan Jogodzinski, The Interrogating the Anthropocene: Ecology, Aesthetics, Pedagogy, and the Future in Ques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xiii-xv.
4 Susan Ballard, Art and Nature in the Anthropocene: Planetary Aesthetics (London: Routledge, 2021), p. 132.
5 Katarzyna Paszkiewicz & Andrea Ruthven (eds.), Cinema of/for The Anthropocene: Affect, Ecology, and More-than-Human Kinship (London: Routledge, 2025), p. xi.
6 Ibid., p. 1-18.
7 Bill Gilbert & Anicca Cox, Arts Programming for the Anthropocene: Art in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9), p.137-138.
8 Anna Lowenhaupt Tsing,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of the Anthropoce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p. 12.
9 Jennifer Fay, Inhospitable Worlds: Cinema in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20.
10 Kaya Barry & Jondi Keane, Creative Measures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Mobilities, and Participatory Geographies (London: Palgrave Mcmillan, 2019), p. 1-24.
11 T.J. Demos, Beyond the World’s End: Arts of Living at the Cross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42.
12 Travis Holloway, How to Liv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ory, Art, and Politics for the Anthropoce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14.
13 請參閱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ume 1: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London: Polity, 2014), p. 2; Yuk Hui, Machine and Sovereignty: For A Planetary Thin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4), p. 186.
14 Edmund Husserl, Manuskripte zur Konstitution von Raumdingen – Aus den D-Manuskripten (Leuven: Springer, 2024), p. 35-70.
15 Vladimir Lenin,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EPUB File.
16 Ibid.
17 Louis Althusser, What Is To Be Done? (London: Polity Press, 2020), p. 23.
18 Alain Badiou & Marcel Gauchet, What Is To Be Done? A Dialogue on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London: Polity, 2016), p. 14-15.
19 Ibid., 26.